第一届胶东散文年选
【 胶东|第一届胶东散文年选最佳作品奖系列—吴殿彬】最佳作品奖

文章插图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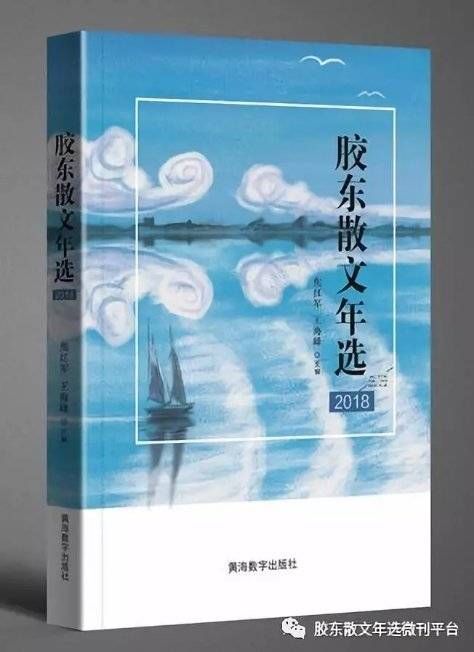
文章插图
我永恒的灯光
文|吴殿彬
煤油灯的灯光如豆,我妈妈却能看得很远很远。
现在很多年轻人很陌生的煤油灯,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家还用着它。1966年的时候,同校的同学到县城看见了电灯,就觉得自己高人一头,站在高台上,咋唬那个电灯比月亮还亮,太亮了,电灯,你知道吗?电的灯!晚上,在昏黄的煤油灯下,我向妈妈报告了这个消息,她的眼睛被煤油灯光照得亮亮的,说:
“你就像现在这样好好念书,一定能到城里去做大事!”
“妈妈,你放心,我一定好好念书。”我郑重地回答着,靠在她的花边机旁,从书包里拿出书来,读书做作业。煤油灯的光红红的,那点如豆的火焰之光,把我和妈妈的身影溶合在一起,照在北墙上。我想起父亲还活着的时候。那时,我还是个刚记事的玩童,还没出嫁的三姐哄着我在炕上玩。叭啦叭啦叭啦……妈妈花边棒槌互相碰撞的清脆的声音,我听着比木琴还好听——这当然是后来的时候了,当时我连木琴的名字还不知道呢——仿佛煤油灯的光,就像电灯一样,妈妈的脸让煤油灯照得通亮通亮的,真好看。我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。我爬到窗台上,把窗户纸捅个眼,从窗棂缝里看天上的月亮。月亮在厚厚的乌云上游走,有时候会从缝隙中探出头来看着我家。我就高兴地叫:“月亮公公看见我了。”三姐怕我跌着,吓唬我说:“快下来,窗外有个老毛猴,咬你。”妈妈说:“别吓着你小兄。”我咯咯地笑着爬下窗台,然后去抓妈妈的花边棒槌……家里充满了姐姐的呵斥声和妈妈的劝告声:“你不会织,别弄乱了线,妈妈不好织啊,快跟姐姐出去玩吧。”姐姐把我抱到院子里,教我:“月亮月亮小小的船……”自从七岁上,父亲因病过世,三姐也早两年出嫁,我的家只剩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了。而我也在苦风凄雨的岁月里,上了小学。我记着妈妈的话,好好学习,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,老师跑到家里夸奖我,给妈妈忧愁的脸上嵌进希望的光彩。“考考考,老师的法宝;分分分,学生的命根。”我的小学老师嘴上念着这句话,天天傍晚放学前都要把当天学的考一考。我每天都是拿着一百分的卷子回家向妈妈报喜。每天晚上,都是在炕上,在煤油灯下,妈妈织花边,我做作业。煤油灯油烧了一瓶又一瓶,妈妈的花边织了一机又一机,月亮转了一圈又一圈,然而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了。先是连地瓜干也吃不饱了,后来接着是吃糠咽菜,到我九岁那年,春天开始上山剥树皮来家当饭吃了。我白天上学,晚上回家,就重复着煤油灯下的故事。而且,每次的故事开头,都是这样两句话:
“儿子,你就这么好好念书,长大了替妈争口气!”
“妈,你放心吧,我一定给你争气!”
只有那天晚上,我把同学到县城看到电灯的事儿告诉母亲后,她第一次改口说,叫我好好念书,将来做大事,而且要进城去。因为那里有电灯吗?还是更能让人看到我为妈妈争了气?此前,我对怎样为妈妈争口气,没有明确的标准,只觉得只要每天考第一,就是为妈妈争气。多少次,家里没饭吃,过年没有新衣穿;多少次夜里我先睡着了,被妈妈啜泣的哭声惊醒。我会替妈妈擦干眼泪说:“妈妈,有你儿子呢,儿子学习好,为你争气。”直到妈妈叹息着夸奖我,看着我,慢慢地,她的眼睛里重新有了勇气和希望的光,我才跟妈妈一起睡下。这时,我把煤油灯芯压到很小很小,就如一粒小绿豆那么大,满屋子只有窗台上这灯光笼成一片淡淡的红色。直到听不见妈妈的叹息声了,我才轻轻地把煤油灯吹熄。
我家的煤油灯跟很多人家的一样,都是从供销社里买的。煤油灯是个啤酒杯粗细的玻璃瓶做的。上面是个带丝口的铁盖子,盖子中间有个筷子粗细的圆孔,里面插着薄薄的铁板卷的灯芯套子,瓶盖上面露一小截,瓶子里一大截;这一大截中间有个孔,好往上提灯芯。灯芯是用吸水性好的纸卷的,从瓶里的套子一直蹿到瓶盖上套子头,露出一块来好点火,瓶子里面的灯芯长,用来吸瓶子里的煤油,用火柴点燃套子里露出来的灯芯,煤油灯就会窜起火苗来,把黑暗照亮。煤油灯盖子下面玻璃瓶的丝口上,缠着两圈细细的铁丝,在一边扭出个长条来打个扣子做灯鼻。每家都有灯挂。我家的灯挂是在一个小方木墩上打了榫口,楔进一根不到三尺高的方形小木杆,木杆上半端钉个小钉。我家也跟别人家一样,在炕头墙上,灶间墙上和门框上,都钉着大钉子,挂灯。晚上,全家人吃饭、拾掇碗筷或者在家里做什么大活,煤油灯便被高高地挂起。高灯矮亮!但是总有一块灯下黑。妈妈织花边的时候,往往不用灯挂,直接把煤油灯放在花边机上。那样,灯下黑的地方便只剩一点点,整个屋子都亮堂着,但最亮的还是花边机。很多时候,灯芯越点越小,妈妈织得快了,花边机的震动会使煤油灯的灯光一跳一跳的,这个时候,妈妈便会停下来,用根头卡子,把灯芯拨一拨,然后把灯盖扭开,用头卡子把灯芯往上提一提。这时,煤油灯的火苗又窜得大了,屋里一片光明。妈妈会对我说:
- 刘 铴:生命最后的呐喊(散文)|00后作品 | 弩之末
- 中华诗词|散文丨家乡的庙子坑
- 茅盾文学奖|“迟子建散文典藏”五卷全新上市
- 满 堂:一篇散文:从落笔到收笔|周四写作课 | 散文
- 人生酸甜苦辣,食物让生活温暖而充满希望|读书 | 冰心散文奖
- 中国散文学会|青未了|散文《感悟南山》
- 当代散文|青未了|留白的哲学
- 散文|散文|蒲光树:棠湖韵味
- 邓颖超|森林故事|苗圃游记(散文)
- 牟尼沟|青未了|散文《走松潘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