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肌肤才能听见的“树木之歌”,诉说着人与自然永恒的联系( 三 )
就像《看不见的森林》里所说的那样:“一切故事都部分包裹在虚构之中——这形形色色的虚构,或是出自简单化的假想,或是出自文化短视(cultural myopia),以及故事讲述者的骄傲。我学会陶醉于故事中,而不是将故事误当作世界明澈而妙不可言的本职。”一个美国生物学教授在亚马孙的雨林里感知的万物之间的联系,其实是西方文化允许他听到的、原住民社群试图表达给他的,以及以我们现有的科技水平所能够触及的。所以《树木之歌》里非常关键的一部分,不是在森林里用耳目去看去听,或者借助仪器去观察和倾听,而是通过与人的交谈来感受这种联系。作者同亚马孙雨林的原住民交谈,同美国曼哈顿大街来来往往的行人交谈,同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交谈。在此过程中,他一直在努力做一个观察者,就像他在《看不见的森林》中所说的,频繁拜访,不惊扰,不干涉,如实记录环境中发生的一切。与此同时,正如人的声音是树木之歌的一部分,人本身也是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,生命网络中无法割裂的一环。个体的人不可能脱离整个网络,他在与树木和原住民建立联系的过程中,编织出整个故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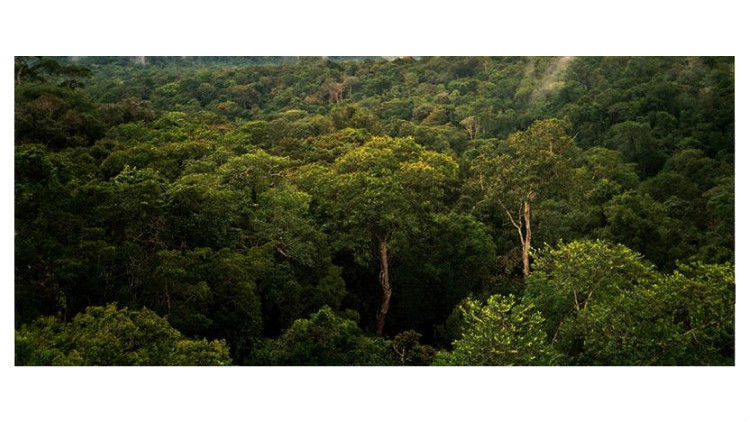
文章插图
亚马逊雨林
《树木之歌》在全球地图上选取了几个地点,包括冲突最激烈和争端最明显的热点地区。比如厄瓜多尔的石油钻井和国家公园森林保护之间的冲突,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建立纽带关系的橄榄树。西方与殖民地原住民、民族国家之间的对立和冲突,是联系的一种形式。“橄榄树”这个章节中有这样一段话:“当人们和树木失去了给予彼此生命的牵连时,肥沃的土地就枯萎了。战争和颠沛流离,不仅仅切断了人和土地的关联。从土地上逃离的人们,也抹杀了土地所承载的知识。因为工业而流离失所的亚马孙的瓦拉尼人,被殖民者杀害和驱逐的北美印第安人,被流放巴比伦的犹太人,浩劫之后的巴勒斯坦人,甚至是和平时代因为利润微薄而导致的农业人口流失……所有这些都导致烙印在人类与其他物种联系之中的记忆,逐渐消失殆尽。流离失所的人们,可以书写出脑海中的东西,并加以保存,但是,那些需要通过持续的关系而产生的知识,在联系断裂的时候就会死去,留下的仅是一个缺乏智慧和生产力,缺少恢复能力和创造性的生命网络。人类在这些混乱和损失之中传承、生活。然而,当我们建立新的关系时,将把生命重新缝合在一起,并增加生命网络的美丽和潜力。在厄瓜多尔,奥米尔基金会在退化的土地上重植森林,重构植物和人类的关系,他们继承了祖辈的知识,并将它们传承给成百上千的年轻人。”
哈斯凯尔作为生物学家和博物学家,并没有过多地评价这些国际上的对立和冲突,但是他从生态学角度得出的结论是:冲突和伤害都是局部的,只是对个体而言的,种种动荡和激变,最终都会达成整个生命共同体的和谐。个体的死亡恰恰是为了整个生命网络的存续。化用尼采的名言,生命网络的特征就是“杀不死我的,必将成为我的一部分”。万事万物之间都存在相互联系,这种生物学观念运用到整个人类社会中,形成了一种逻辑自洽的道德体系。
生命网络表述的,通常是一种建立在不确定性上的永恒。比如一株菜棕,它“扮演了《圣经》中被称为傻瓜的角色,在沙子上建立生命,借此度过一生。一棵菜棕的生命,通常长于一个世纪,在它死亡之时,它发芽那时的地貌早已改变。这不是悲剧,而是沙质海岸必经的历程。我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这点,但事实上海浪的力量和沙子的流动,塑造了菜棕的每一部分的‘存在’。不论是它的身体,它的果实,它的幼苗期,它叶片细胞中的化学物质,都植根于此。”这样一种流动中的永恒,或许能避免虚无主义导致的绝望。
个体总会消亡,但生命网络中的联系会永远延续下去。“死后还有生命存在,只不过并非永生。”死亡并没有终结网络间的联系。“当树木腐烂时,死去的原木、树枝和树根成了成千上万种关系的焦点。森林里,至少有一半的其他物种,在树木横陈的尸体上或枯木内,寻找食物和家园。”
- 金轮法王为何需一日一夜才能伤慈恩?看看周伯通,或许能明白
- 我们要怎样才能读懂《诗经》以《羔羊》这首小诗为例聊一聊
- 多肉淋水后,哪些事情不该做,早知道才能避免“发烧”
- 唐僧念的紧箍咒到底是什么意思译成中文,你听见也头疼!
- 5种耐热耐晒的开花植物,光照充足才能养好,春季可考虑种下去了
- 怎样才能制作出‘苍劲古朴’的枸杞盆景
- 金边瑞香开完花后,下一步要如何养护?植株才能长得旺盛
- 那些流失在海外的“国宝”,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归祖国的怀抱
- 当美术生也是海贼迷,作画只有资深粉才能懂,网友:太熟悉了
- 玩弄盆景,怎样才能达到自己理想的造型?三是重点不容忽视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