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掘显示,东先贤遗址包含了商代中期到晚期的遗存,为“祖乙迁邢”的说法提供了年代上的证据,我们算是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
跟随刘绪老师读完硕士、博士,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,离北大不远,所以经常回学校和刘老师聊天。到了饭点,我们就一起去吃饭。那时候,北大西门外还有一些小饭店,经常是师徒二人一人一碗面,后来也常去校内的畅春园食堂和勺园。谈话的内容五花八门,有时谈考古新发现,有时谈我的工作生活。他也经常谈自己的研究心得或新发现的问题,嘱我回去仔细整理写出论文。
2019年9月,刘绪老师确诊肺癌。我只在他第一次化疗之后的某一天,得以陪床一日。上午输液,刘老师闭目养神,偶尔谈话,主要讲的是前段时间考察几处考古工地的情况。住院之前的几个月,他一直在考古发掘现场,那时他的胸部已偶尔疼痛,但他依旧没有离开工地。近来我时常想,如果他提早一点去医院治疗,这个病能不能治愈呢?毕竟,我认识好几位肺癌患者,后来都痊愈了。
那天下午,他专门谈了三代都邑考古问题,指出种种现象和变化,命我回去整理成文。他还告诉我,趁着化疗之前的几天时间,他在病床上赶出了一篇序文,“已经答应人家了,化疗以后不知道啥情况,耽误了不好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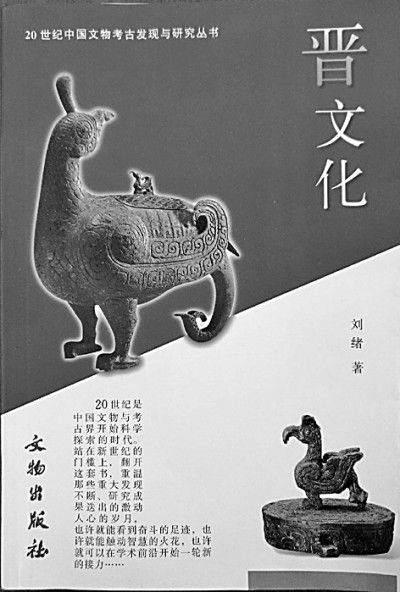
文章插图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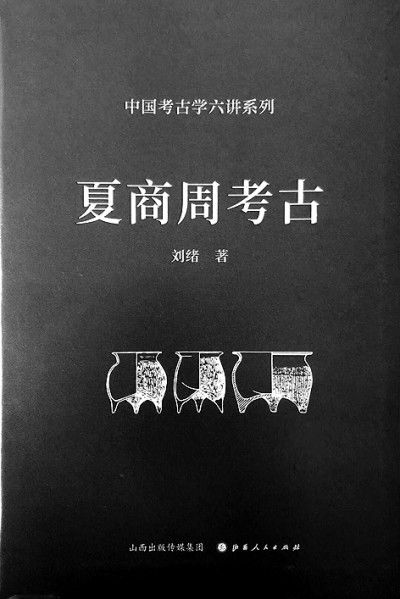
文章插图
二
刘绪老师常说,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的根,也是考古学的生命力所在,不做田野就成不了真正的考古学家。50年来,全国很多考古工地,都留下了他瘦削的身影。
20世纪70年代在北大读本科时,刘绪老师就参加了湖北黄陂盘龙城的发掘。他当年的工作日记和探访记录如今就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馆陈列着,这是对考古学家最好的纪念。本科毕业后,他到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工作,又参与发掘了大同方山永固陵、夏县东下冯、沁水下川等遗址。
1980年,他考取邹衡先生的研究生,回到北大,从此之后,几乎每年都跑田野,多则半年,少则几个月。
入学不久,邹衡先生便派他去山西曲村参加发掘。留校工作后,他又以辅导老师的身份,在曲村遗址带学生实习。曲村是他工作时间最长的考古遗址,前前后后将近20年,正是在曲村,他培养了一批从事田野考古的学生。
20世纪90年代中期,刘绪老师开始了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的发掘。这是一处西周燕国都城遗址,也是邹衡先生拼命保护下来的遗址。多年的发掘工作,使他对琉璃河遗址充满感情。2018年,琉璃河考古重新开展,他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前往琉璃河工地,一方面指导新的发掘,一方面整理发掘资料。在罹患重病的最后两年里,他利用放疗化疗间隙,完成了房山琉璃河遗址发掘报告的初稿。2021年12月19日,刘绪老师去世两个多月后,在电视台的一个直播节目中,几代考古人回忆起刘绪老师在琉璃河的考古活动,与他共事多年的北京考古所赵福生先生泪洒直播间。
从20世纪末开始,因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需要,刘绪老师又先后参与了陕西周原、周公庙遗址和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、禹州瓦店遗址的发掘。2012年退休时,他以为田野工作会减少,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会变多,计划将自己多年考古的认识进行系统整理。但是,每年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老师们带队田野实习,总是希望刘老师能去做辅导教学。有他在工地上,他们心里才踏实。地方上的考古队同人,听说刘老师退休了,也纷纷在工地发掘或整理期间,请他去指导。如此一来,原本的退休计划很快就泡了汤,他仍然奔波于考古工地,甚至比以前还要忙。
刘绪老师早年的生活很艰苦,身体一直不太好,常年胃病。20世纪70年代在发掘方山永固陵期间,就曾病倒在工地上。在天马—曲村、琉璃河、周公庙等考古工地上,他也不止一次生病。只要身体稍好,他就立刻回到工地,辅导学生,解难答疑。
刘绪老师说,这么多年,只有一次,他动摇过。那是在曲村考古工地,徐天进老师正在发掘的墓葬突然塌方,徐老师被深埋在地下,20多分钟后才被抢救出来送往医院。刘老师当时情绪低落,在回宿舍取徐老师的换洗衣物时,脑子里闪现过退出的念头。徐老师获救后,刘老师又和过去一样投入田野工作之中。
多年的田野考古实践,使得刘绪老师对田野考古现象的判断准确率非常高。按照他的指导进行发掘,通常不会造成发掘破坏。他也熟稔相关考古资料,对新材料学术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准确深刻。在考察发掘现场,他会把自己的看法无私地告诉工地负责人,帮助他们分析资料,解决难题,顺利地编写考古报告。
- 文化节|沪上首家传统文化传承中心——“北站传统文化传承中心”揭牌成立
- 盐水|4种肉、菜直接用水洗当心越洗越脏!厨房老手都做错了
- 红炉|潍坊新华中学用“心”继承传统,以“爱”温暖冬日
- 文明|初始于心,长践于行——44中学寒假开展文明实践“五个一”活动
- 感染力|民进巴中市委会主委秦渊:用文学艺术的感染力凝心聚力
- 维生素c|吃动物内脏有害健康?能不能放心吃?真相来了
- 拔节而上 瓣瓣同心|京津冀协同发展八周年 ·长图 | 协同发展
- 柳绵|苏东坡是如何一步一步寻得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生命归宿的?
- 蛋挞皮|蛋挞小点心
- 讲堂|地矿一院地勘中心道德讲堂开讲
